 PDF(1357 KB)
PDF(1357 KB)


Development, 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 Path of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of Chinese Sports Training Science
PENG Guoqiang, ZHOU Zhibo
Journal of Capital University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Sports ›› 2025, Vol. 37 ›› Issue (1) : 1-9.
 PDF(1357 KB)
PDF(1357 KB)
 PDF(1357 KB)
PDF(1357 KB)
Development, 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 Path of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of Chinese Sports Training Scienc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onstructing China’s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explore the theoretical problems of constructing China’s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of sports training, improve the scientific level of sports training and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ompetitive sports. The research holds that the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of Chinese sports training is formed on the basis of learning from foreign advanced training theories and taking root in Chinese sports training practice, which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ocalization, innovation, systematization and practicality. The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of Chinese sports training science has experienced four evolution stages: initial exploration, independent innovation, systematic improvement and digital transformation. There are practical problems such as research paradigm valuing“qualitative” over“quantitative”, knowledge generation valuing “grafting” over“endogenous”, and theoretical application valuing “abstract” over “practical”. The research puts forward: 1)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frontier of sports training science in the world and the practical needs of China’s sports training field, adhering to Marxist theory as the guidance, planning the top-level design of the construction of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of Chinese sports training science with systematic thinking; 2) Build an academic community of sports training research to strengthen the organizational guarante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of Chinese sports training; 3) Improve the independent innovation ability of research subjects in the field of sports training, and the methods and ways of enabling the construction of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of Chinese sports training science b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4) Promote the cross-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of“sports training +”and consolidate the talent bas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of sports train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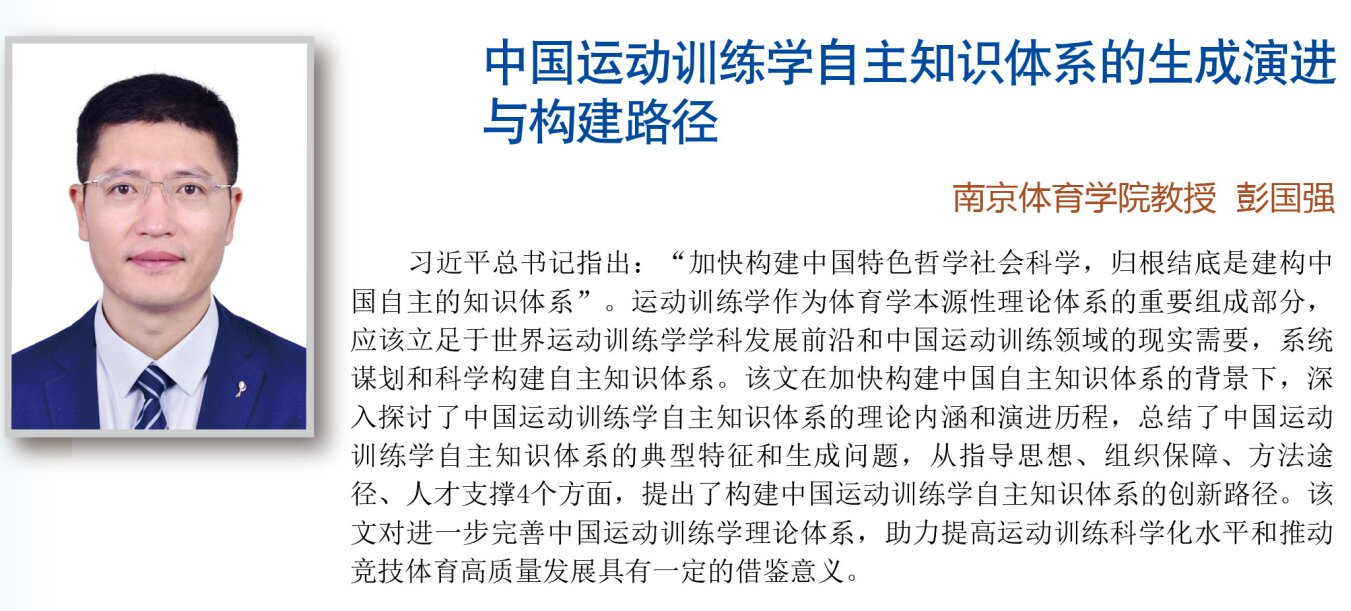
Chinese sports training science /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 Generation and evolution / competitive sports / new nationwide system
| [1] |
鲁长芬, 韩贝宁, 罗小兵. 标识性概念与中国体育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J]. 体育科学, 2024, 44(8):22-32.
|
| [2] |
张雷声, 韩喜平, 肖贵清. 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J].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 2022, 8(7):4-16.
|
| [3] |
姜哲, 黄汉升. 中国体育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多维镜鉴、现实审视与探行方略[J].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2023, 46(9):1-14.
|
| [4] |
黄汉升. 论体育学期刊与中国体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J]. 西安体育学院学报, 2024, 41(4):421-429.
|
| [5] |
曹景伟, 席翼, 袁守龙, 等. 中国运动训练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J]. 天津体育学院学报, 2003, 18(2):43-50.
|
| [6] |
田麦久. 运动训练学发展历程的回顾及21世纪展望[J]. 体育科学, 1999, 19(2):33-36.
|
| [7] |
曹景伟, 袁守龙, 席翼. 运动训练学理论研究中的中国流[J]. 体育科学, 2004, 24(2):29-32.
|
| [8] |
王村, 钟敏. “三从一大”运动训练原则的发展与贯彻[J]. 武汉体育学院学报, 2004, 38(3):75-77.
|
| [9] |
陶于. 关于竞技体育学与运动训练学理论认识问题的思考[J]. 体育学刊, 2008, 15(11):84-87.
|
| [10] |
田麦久, 刘大庆. 熊焰竞技能力结构理论的发展与“双子模型”的建立[J]. 体育科学, 2007, 27(7):3-6.
|
| [11] |
田麦久. 辩证协同运动训练原则的缘起与确立[J]. 中国体育教练员, 2019, 27(2):3-8.
|
| [12] |
刘大庆, 张莉清, 王三保, 等. 运动训练学的研究热点与展望[J].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2013, 36(3):1-8.
|
| [13] |
张莉清, 刘大庆. 近5年我国运动训练学若干热点问题的研究[J]. 体育科学, 2016, 36(5):71-77.
|
| [14] |
胡海旭, 杨国庆. 数字化转型:点燃当代竞技运动训练变革新引擎[J].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2021, 44(11):81-98.
|
| [15] |
仇乃民, 李少丹. 走向大数据时代的运动训练科学研究[J]. 首都体育学院学报, 2015, 27(6):541-545.
|
| [16] |
杨国庆. 整合分期:当代运动训练模式变革的新思维[J]. 体育科学, 2020, 40(5):3-14.
|
| [17] |
闫琪, 廖婷, 张雨佳. 数字化体能训练的理念、进展与实践[J]. 体育科学, 2018, 38(11):3-16.
|
| [18] |
钟亚平, 吴彰忠, 陈小平. 数据驱动精准训练:理论内涵、实现框架与推进路径[J]. 体育科学, 2021, 41(12):48-61.
|
| [19] |
董德龙, 杨斌. 中国运动训练学需面对的3个问题:学科内容、研究范式与知识建构——基于一种双重转型的考虑[J].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2015, 38(3):126-131.
|
| [20] |
李宝泉, 李少丹. 中国运动训练理论发展的困惑与选择[J].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2014(1):139-144.
|
| [21] |
黑马科学训练坊. 运动与训练科学C刊年报(2024汇总)[Z/OL]. (2025-01-02)[2025-02-12]. https://mp.weixin.qq.com/s/n9aDAqChaE8rSAIu_mLXog.
|
| [22] |
赵鲁南. 我国运动训练理论研究的历程及现代特征[J]. 体育文化导刊, 2013(9):63-66.
|
| [23] |
吴贻刚. 近30年我国运动训练理论研究述论[J]. 上海体育学院学报, 2008, 32(4):14-17.
|
| [24] |
夏之顺, 张莉清, 张世超. 我国《运动训练学》教材的历史发展、现存瓶颈与建设路径[J]. 武汉体育学院学报, 2024, 58(10):89-96.
|
| [25] |
刘曙光. 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方法论自觉[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60(5): 5-17.
|
| [26] |
曲鲁平. 我国青少年体质健康促进模型构建与运动干预研究[M]. 北京: 人民体育出版社, 2021:17-22.
|
 PDF(1357 KB)
PDF(1357 KB)
 图1 中国运动训练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路径
图1 中国运动训练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路径/
| 〈 |
|
〉 |